:儒家生命智慧的伦理性阐释人是生命的存在
:儒家生命智慧的伦理性阐释人是生命的存在
儒家生命智慧的伦理性阐释人是生命的存在,生命的存在是具体和现实的。马克思说:“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的本质即自己的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 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具体的、现实的、感性的存在是人生命活动的基础。人还是精神性的存在, 人的精神性存在是对现实、感性存在的超越, 这种精神超越性透视着人的生命智慧。孟子“浩然之气”所蕴聚的人的生命智慧, 就在于他首先是肯定了人存在的这种具体而现实的特征, 即“气”存在的感性特征, 同时也肯定了人存在的自然生命现象;孟子肯定“气”的感性存在并不是目的, 目的在于肯定“气”背后所内在蕴聚着的人的精神生命, 在于论证“浩然之气”所显现的人的内在精神品质和超越性结构, 从而展示他对人的生命智慧的深刻理解和体味。创生性体验与“生命”生命智慧的形而下层面是人的现实生命活动, 其理论层面便是生命哲学。生命智慧应该首先肯定“生”, 故《周易·系辞上》曰:“生生之谓易。”《周易·系辞下》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这说明天地自然以及人的存在都是以生命的存在为根基, 天地自然的不断衍生所展示的根本精神就在于化成生命, 自然的生命存在也化成了人的生命活动, 因为人的生命活动的现实基础就是自然性的存在, 所以人生命的激情与活力放射又展示着人对天地自然的认同, 以及创造生命的精神性品格。
对生命智慧的理解可以有三个层面, 即对生命本体存在状态的把握;对个体生命存在的体验;以及对人的精神生命的超越性结构的体认和践履人生活动的价值。从生命存在的本体性角度讲, 以天地自然生命为表征的宇宙生命存在的基础, 当它运演到人的生命活动中时, 就表现为人的自然生命和精神生命的一体性构成, 它表现了生命结构的存在性和创生性的统一, 而创生性又是生命衍化的终极趋向。从个体存在的生命体验形式来讲, 把握生命智慧首先是要肯定生命的个体性存在, 因为现实、具体的生命形式首先是个体的, 只有这种个体生命的存在才使生命具有了活力, 具有了丰富多彩性。个体生命的体验是以自然生命体验为基础, 但趋向终极存在的生命并不只是肯定生命的存在性, 而在于体验创生性, 同时只有在创生性体验中, 人才能把握生命的智慧, 创造生命的价值。从体验人的精神生命及践履人生价值角度讲, 要求人在创生性体验中必然要展示生命精神的品格, 这是人生的意义, 是人生存活动的未来指向, 但他又必然体现人生命的整体性, 因为他是由自然生命和精神生命的合体“气聚”而生, 并非是先天而就, 必须是后天的养成, 故孟子提出要“养气”。重视“生”及“生命”的存在是中国传统文化生命智慧的精华, 同样也是儒家文化的精华。
孔子在《论语·子罕》中曾发出过深深地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看起来这是孔子对时间流逝的一种感叹和领悟, 从更深层次上看, 这是孔子对人的生存智慧的一种感悟。儒家对“生”的理解是动态的, 《论语·颜渊》中所说的“死生有命”, 就是在“死”与“生”的对立关系中肯定了“命”的特性。这里既肯定了“命”作为自然宇宙规律性存在的本质, 同时也肯定了它与“死”与“生”的动态运作过程。在儒家先人那里重视的更是“生”, 他们强调在“生”的命定中展示生命的价值, 故孔子说:“未知生, 焉知死?” (《论语·先进》) 孔子论“知生”, 一方面是肯定生命的客观存在, 另一方面则是把握生的意义, 即人“为什么活”的问题。儒家先人并不奢谈“死”, 他们往往是在与“生”的对称中, 或者是从比较意义上来谈“死”。荀子也说:“生, 人之始也;死, 人之终也。终始俱善, 人道毕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终。终始如一, 是君子之道, 礼义之文也。” (《荀子·礼论》) 荀子在这种对比的意义中讨论生死问题, 并且用道, 用礼义的尺度进行衡量, 要求人应该是“敬生”而“慎终”的。如果说这种“生”与“命”之义在孔子那里还有抽象意义上的“神”的意味, 或是显现形而上层面的话, 那么在孟子, 乃至荀子那里, 由“心”与“性”而推演出的“命”就具有了人之肉身存在的特征。
孟子的“心”论有本体的意义;其“性”与“命”具有“心本体”的具体化、现实化的意义。孟子说:“仁之于父子也, 义之于君臣也, 礼之于宾主也, 知之于贤者也, 圣人之于天道也, 命也, 有性焉, 君子不谓命也。” (《孟子·尽心下》, 以下所引孟子语, 皆只注篇名) 他还说:“莫非命也, 顺受其正……尽其道而死者, 正命也;桎梏死者, 非正命也。” (《尽心上》) 孟子称的“正命”, 即为“尽其道”之命。所谓“尽其道”, 无非就是儒家的“仁义”之道, 这种“道”为人的生命存在注入了无穷的活力和巨大的能量。当代新儒学大师牟宗三曾认为, 中华民族的灵魂在于首先把握住“生命”, 其特别注意的是如何调护生命、安顿生命, 这就是“仁的文化系统”的基本内涵和以入世为本的生存智慧的基本特性。在孔、孟那里不仅强调了要善待生命, 更强调了要在仁、义、礼、智、心等德慧术知中体验生命的价值。因此, 孔、孟常常要发出“舍生取义”的感慨。孔子就说:“志士仁人, 无求生以害仁, 有杀身以成仁。” (《论语·卫灵公》) 孟子也说:“生亦我所欲也, 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 舍生而取义者也。” (《告子上》) 这里的生命作为一种超越性结构, 就不仅是以“气”而构筑的自然生物性的存在, 更重要的是由于“仁”与“义”的存在, “生”便转化为一种“生成”的意义, 而被内在化、人格升华了, 生成为精神性的存在, 体现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倡生与做人内在统一的生命活动。
《荀子·王制》中说:“水火有气而无生, 草木有生而无知, 禽兽有知而无义, 人有气、有生、有知, 亦且有义, 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串接的“气”到“义”的生命逻辑链条, 实际体现了人的自然生命本体和以“义”为中心的精神生命本体的存在样态, 也回答了人何以为人, 又何以“最为天下贵”的原因。儒家文化对生命存在和生命精神的体认, 体现了中国人的一种生存智慧, 并且是在自由自觉意义上, 将人的自然生物性存在升华为伦理道德体验, 从而又转化为带有艺术化、审美化的生命存在。杜维明曾评述这种精神说:“儒家所讲的做人的道理, 其目的就是要把人的生物的存在, 经过长期的自我奋斗, 转化成一种艺术的存在。所谓‘七十而从心所欲, 不逾矩’, 就是把自己的生物性要求和最高的道德理想要求合在一起。”以“志”“气”来创造生命在中国古代的学人那里, “气”的存在既有本体论的意义, 也有认识论的意义。从本体论意义上讲, 它展示宇宙生命有机体的存在样态, 故《说文》释为:“气, 云气也”。从认识论意义上讲, 它又是对生命有机体的规律性的把握方式。这样, 它既是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 又是人生的一种体验方式。《管子》的“精气”论讲道, 人是天精地形造和而成, 人所内聚的精气越多、越充足, 其生命力就越旺盛, 就越富有智慧。
“气”在孟子那里, 除具有古人论“气”的普遍意义外, 还具有自身特殊的内涵。孟子将“气”作为人生命存在的一种精神现象, 作为人格品质的表征, 作为充实之美的载体, 是具有深刻的审美内涵的。“气”在孟子那里蕴聚成“浩然之气”, 而所谓“浩然之气”更是从生命的体验形式上, 把握人作为宇宙生命有机体而存在的特殊样态。孟子在与公孙丑讨论“志”与“气”时讲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当公孙丑问及孟子, “何谓浩然之气”时, 孟子回答说:“难言也。其为气也, 至大至刚, 以直养而无害, 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 配义与道;无是, 馁也。” (《公孙丑上》) 这里, 孟子首先是将“气”视为人之自然生命存在基本状态, 是人的精神生命的基础, 是人的精神存在的支撑。但孟子又不是仅仅从人的自然状态谈生命, 他对生命存在的感悟与理解的至深之处更在于体验这种“气”, 显然, 他是将“气”作为一种过程来理解。因此, 孟子往往将“气”与“志”作为辩证一体的存在形式来掌握, 然后才深刻的论证“气”的内涵。孟子说:“夫志, 气之帅也;气, 体之充也。夫志至焉, 气次焉;故曰:‘持其志, 无暴其气。” (同上) 在孟子这里, “志”的统帅作用和引领作用, 与“气”的充实、丰满意义和内蕴着的人的无限的生命活力的作用是一体的。
关于这种“气之充”的意义在《管子》那里已有论述, 《管子·心术上》说:“气者, 身之充也”。“充不美, 则心不得。”管子检验到了这样的现实, 即人是孕气而生, 所以气愈充沛, 人就愈富于活力, 就愈充满了生命的智慧。孟子显然是发展了管子的学说, 他的志与气是融会统贯的, 其中一精神, 一物质;一精神生命, 一肉体生命都绝好地统一了起来。气流动、蕴聚在生命的统一体中, 尽管“志”欲展示人的精神品质, 但无“气”, “志”则无以成事实, 其“志”也无以存在之根基。同时即便是有志的存在, 没有气也缺少存在的依据, 其志必将成为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 志便会成为虚幻的现实。从这种意义上讲, 气与志是互为前提, 相互作用的, 这展示了孟子通过对人之生命存在的体验和把握, 从而深刻体认着那种人的生存智慧。但如何形成这种“至大至刚”, “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呢?孟子讲到他要“善养”这种“气”, 并且是“以直养而无害”。实际上, 这种“浩然之气”已经不是前面所述的处于次位的“气”, 而是内蕴着“志”的“气”, 是人的自然生命和精神生命的有机构成体, 是展示着人的存在性和创构性之统一的“气”, 所以孟子才说, “我善养浩然之气”。
但孟子所“善养”的这种“气”, 并不是凭空而就的, 而是靠他的“养心”而得, 也就是说, 作为生命体验是通过“养心”而得“养气”, 这既是一个生命发展的过程, 也是一个逻辑的过程。因为作为“浩然之气”的重要内容, 具有“帅”的作用的“志”, 必须由“心”而得。无“心”而无“志”;无“志”亦无“浩然之气”。就此, 孟子还认为, 人只有“养心”才能知性知天, 所以他说:“尽其心者, 知其性也。知其性, 则知天矣。” (《尽心上》) 显然这种“心”成为人生命存在的内在机制, 尤其是精神生命存在的根本, 人必须在生命活动中培养这种具有善良本心的品性, 作为人之生存的本性, 所以要“存其心, 养其性”。而君子所具备的性, 就是“仁义礼智本于心”而演化、生成的性 (同上) 。孟子由“养心”到“养气”的生命体验过程起码关注了这样几个层面。首先也是最为基础性的层面即为“寡欲”, 孟子要求先解决人的自然生命问题, 即摆正生命存在的自然活动状态的位置, 他说:“养心莫善于寡欲。” (《尽心下》) 人如果放逐自己的欲望, 让自然生命活动状态占据了主要生存空间, 就必然会消解所必须具有的道德天性, 而使自然性挤压人的精神生命的存在空间。

其次, 是“立志”, 并发扬“志”之帅的作用, 从而凸显人之精神生命的存在空间, 这不仅是要“穷独达兼”, 要“舍生取义, ”更要体现“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滕文公下》) 的精神。最后, 孟子的“养心”必然要求有“存心”, 要强化生命活动的内在机制。他说:“君子所以异于人者, 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 以礼存心。” (《离娄下》) 人所存之心, 所养之心, 具体说来就可以是“则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四心”, 而“四心”作为仁、义、礼、智本性之“端”, 是君子必须具备的, 也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 (同上) 的主要原因, 假如无此“四心”便为“非人”。孟子在这里所说的“端”, 有他在“性善论”思想中所把握的人潜在的向善能力的先在因素, 但这“四心”之所以是人应该具有的仁、义、礼、智的本性之“端”, 就在于人的这种种本性还需要后天的养成, 也就是说, “性善”还只是潜在力, 人还要锻铸后天的养成力, 所以就需要“养心”。但“养心”还不是目的, 实际上, 目的是在于养成充实而有光辉的“浩然之气”。“乐生”—品味情理交融的“乐生”智慧中国传统文化中深深贯注着一种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往往将人生之乐与忧、与责任意识相通联、相融汇, “忧乐圆融” (庞朴语) 可以使人在快乐的人生体验中感悟生命的智慧。
《周易·系辞上》曰:“乐天知命, 故无忧。”这是强调了人应该以一种达观的态度, 超越现实功利, 致力于把握自然存在与生命活动的规律, 这将会是自由而无忧的, 所以李泽厚称中国文化 “乐感文化”是不无道理的。我们将快乐的人生体验作为一种生命境界, 同时我们也可以称其为“乐生”智慧, 在孟子所构筑的充实而有光辉的“浩然之气”中, 就时时显现着这种充满“智慧”的快意人生。快意的生存是人生之大乐事。何谓快意生存, 儒家学者会给予回答:它必然是深刻地进行仁、义、礼、智的道德体验, 并且是在这种体验中获得人生的快乐。为了实现这种人生目的, 或者说是“求道”, 孔子一生发愤努力, 孜孜以求, 他自己就称“发愤忘食, 乐以忘忧, 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论语·述而》) 。作为快意的人生, 把“求道”演进到“体道”, 是儒家乐道精神的中心主旨。求道、体道到乐道作为儒家智慧之一隅, 既可以是人的生命活动的结构性存在方式, 也可以是一种生命活动的境界。具有理智性意义的“道”构筑了生命存在的价值主体, 具有情感涌动的“乐”, 不仅可以使这种“体道”充满无穷的情趣意味, 而且还可以在生命活动的节奏与韵律感中体味生命意义的真谛。
这种“道”配以“乐”, 就可以将人的感性之“乐”升华为具有“道”之理性内涵的精神之“乐”。在孔子那里, “求道”与“体道”固然是十分重要的, 是可贵的人生精神, 是人当以终身之追求的志向, 但由于“道”是外在于人的, 那么人要把“道”内化为自身的内在活动和生命意义的追求, 就必然将其视为快乐的活动, 因此, 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论语·雍也》) 《礼记·乐记》中也称, “君子乐得其道, 小人乐得其欲”。“乐道”的内涵中有理有情, 那么它就必然要“乐生”, 人不在快乐的生命体验中, 也无法体验和创造出有价值的生命。李泽厚在论述中国文化中这种特有的“乐感文化”时, 称这种现象是“情理深层结构”, 他认为, “儒学之所以既不是纯思辩的哲学判断, 也不是纯情感的信仰态度;它之所以既具有宗教性的道德功能, 又有尊重经验的理性态度, 都在于这种情理互渗交融的文化心理的建构”。我认为, 在善养“浩然之气”的孟子那里, 也是将这种“养心”与“养气”作为生命活动的乐事, 孟子也在体认这种情理互渗交融的生命精神的结构性存在, 从而构筑他的这种既非纯思辩, 又非纯情感状态的;既具有对人生理性经验和意义的感悟, 又有对道德信仰追索的“乐生”智慧。
这也说明儒家学说为什么要赋予生命“以雄伟阔大的宇宙情怀和巨大情感、肯定意义 (李泽厚语) 的原因。我们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把握孟子对这种快意人生的体验。首先, 孟子将“乐生”与人生之志相联系。他认为, 人作为“大丈夫”, 必然要“居天下之广居, 立天下之正位, 行天下之大道;得志, 与民由之;不得志, 独行其道。” (《滕文公下》) 具备这种特立独性的人生之志, 并同时配以“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品格, 无疑是人生之大乐事。其次, 孟子将追求道德体验的人生快事与人的自然感性生命体验和追寻群体生存境遇相联系, 因而不是将“乐道”作为孤立的生存体验活动。他认为, “理义之悦我心, 犹刍豢之悦我口” (《告子上》) , 这都是人生之快事。同时他还讲到:“君子有三乐, 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 兄弟无故, 一乐也;仰不愧于天, 俯不怍于人, 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三乐也。” (《尽心上》) 显然, 群体共在与交往活动是人之道德活动之外的快意行为。再次, 孟子所求的人生乐事的较高境界是“诚”, 他把“诚”称为“天之道”, 把“思诚”, 称为“人之道”, 那么, “至诚”就必然会深深地感动他人 (《离娄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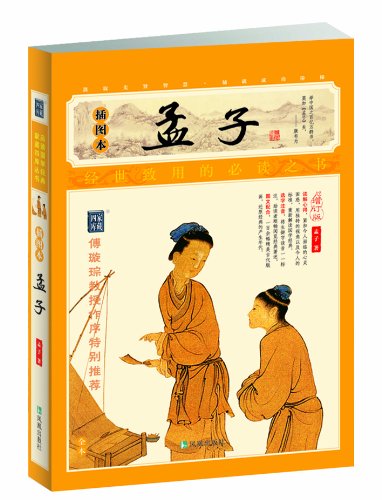
因此, 他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 乐莫大焉。”第四, 孟子还强调“乐”在人生活动中的社会意义。在《梁惠王下》中, 在与齐宣王讨论快乐原则时, 他谈到“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 “人乐乐”不如“与众乐乐”的思想, “与众乐乐”就是要求封建帝王的“与民同乐”。孟子认为, 帝王只有“与民同乐”, 只有“乐民之乐”, “忧民之忧”, 自己才能“乐”, 即“与偕乐, 故能乐”。这样百姓便会“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 于是便可以“王天下”。孟子的这种“同乐”意识不是孤立产生的, 而是他的“配义与道”的思想的具体化、现实化, 既是他“乐生”的体现, 也是他不断充蕴“浩然之气”的社会现实基础。最后, 我认为, 在这种种求乐活动中, 体验“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方是孟子“乐生”智慧的终极所在, 也是他对自我的一种终极关怀, 从我们的分析中可以看出, 孟子追寻的“乐”不是人的自然感性的“乐”, 而是理性之“乐”, 是精神之“乐”。孟子的“乐生”智慧实际也是一种生命体验意义上的精神智慧。它以人生的快意存在和情感体验而使生命注入了活力, 而不是将生命单纯视为自然存在的本真, 而是人生意义和价值的追求。
实际上, 孟子已经把这种“乐”的生命体验形式升华为艺术和审美的境界。充实而有光照体验“生生”是人生之大美, 实际也是体验具有节律特征的生命运动形式, 这是儒家学说中生命美学智慧的真谛。生命美学是以生命哲学为理性内涵的生命智慧的升华及终极状态, 《周易·大畜》曰:“刚健笃实, 辉光日新。”这种思想便突出了儒家那种独特的生命美学精神。我们知道, 孟子的“浩然之气”并非只是对一种善的评价, 作为他的生命智慧的集中展示, 它更是一种“至大至刚”的, “以直养而无害”的人生境界, 它深蕴着审美之维, 或者说, 是一种美学精神的展示。不可否认, 孟子对美的理解无法脱离他终生对道德智慧的体认, 但当孟子将美视作人的一种生存状态时, 他对美的把握也同时具有了生命的意义。尽管他的“浩然之气”, 是“集义所生”, 同时要“配义与道”的, 实际上“浩然之气”更是充实而有光辉之“气”。与此论具有相同意味的是孟子与浩生不害的一段讨论, 孟子谈到:“可欲之谓善, 有诸己之谓信, 充实之谓美, 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 大而化之之谓圣, 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 (《尽心下》) 这里, 孟子已经将“充实之谓美”放在了“善”与“信”这些做人的一般道德原则之上, 也就是说, 把美视为道德活动之上的一种人格存在。
在孟子看来, 人的这些“善”与“信”的道德体验必须是充实的方才是美的。我们认为, 充实实际也就意味着是生命活动的充实, 这内蕴着审美的维度。孟子进一步讲到了“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 这里的“大”不是一般性的善与伦理意义上的“美”, 实际上, 这是对一般美的超越, 是一种“大美”, 是“至大至刚”的“美”。它既要浩然充实, 又要辉光四射, 充盈浩大, 只有这样“美”才可以体现生命的意义, 才可以达到更高层次的人生境界。人具备这种生命的智慧, 并不是就此而止, 而是必须将这种人生的能量释放出来, 那么如何释放呢, 孟子要求人要有为“圣”之道, 即将这种充实而有光辉的生命体认化育天下, 润泽天下。这种化育, 这种润泽应该是细细地、神秘地、不见痕迹的 (有“羚羊挂角, 无迹可求”的样态) , 或者说, 就是一种自由自觉的状态, 试想, 这不正是一种审美的过程吗?如果我们只是在“充实之谓美”的字面意义上去理解孟子对美的体认和把握, 实际视野是狭窄了。这里我们完全可以看到, 由善、信到美、大再到圣、神不正是美的节奏与韵律的动态合奏吗, 是人之生命活动的律动吗?这种生命的律动又是由以善、信为载体的伦理道德活动, 而向大美的审美活动的逻辑演进, 这表现了美的内化过程, 但它又不是目的。
“大美”还必须外化, 外化为人的现实行动, 并且是一种“大化”, 是“不可知之”的“大化”。在这里, 具有“充实而有光辉”的“大化”之美是人内蕴着的勃勃生机的、动态的生命存在状态, 由圣而神的律动则是赋于生命节奏以韵味无穷的生命回应和绵延生长的神韵美姿, 这就充分展示了生命节律的逻辑的运演, 同时也体现了美作为人类生命精神的本质。孟子以“浩然之气”作为生命智慧的内在结构, 它所体现的“充实而有光辉”的生命美学精神具有阳刚之美的风范, 这是儒家人格理想的一种形象化体现。中国古代的人格理想大都是以这种阳刚之气灌注内在的精神品质, 但它们更多地却是以“天”本体为其基本内容, 以伦理理性意义为行动指归的阳刚之气。即便是《周易》中的“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论述, 也主要是强调君子以“天”本体为参照, 以自然运行的规律, 激励自身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动和人的现实行为。应该说, 孟子以不断地“养气”为生命活动指向的人格风范所涵蕴着的阳刚之气更具有超越性意义, 原因就在于他内存有精神体验性和生命节律性所展示的美学精神, 因此, 它超越了一般的自然本体的存在样态和伦理意义, 而被艺术化、审美化了, 这一点对中国后世的艺术与审美思想的影响尤为重要。
魏晋曹丕的《典论·论文》就说:“文以气为主, 气之清浊有体, 不可力强而致。”曹丕强调了文艺审美活动中主体的精神品质和个性之气所展示的生命节律。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干脆就有《养气》篇, 他说:“志盛者思锐以胜劳, 气衰者虑密以伤神, 斯实中人之常资”。“是以吐纳文艺, 务在节宣, 清和其心, 调畅其气。”刘勰将“气”与人的精神活动相联系, 将“气”与“神”并称, 将“气”视为生命体验的内在素质, “神”视为“气”的外在表现。人只有“清和其心, 调畅其气, 才会“理融而情畅”, 这种具有无穷韵味的生命节律性的审美体验方式, 实际是需要不断“养气”而得, 并且一定会是“充实而有光辉”的“浩然之气”, 否则便难以“畅气”, 乃至“畅情”。其实, 在生活中又何尝不是这样, 人如果能从本质意义上去“畅气”、“畅情”, 那么就必然会展示“充实而有光辉”的生命精神。在中国美学的发展过程中, 将审美活动作为生命美学体验, 并将这种体验推向极至的, 当属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宗白华的美学实际就是生命美学, 他的审美体验实际也是生命体验, 他的美学思想时时渗透着对宇宙生命的无尽关怀和对生命存在的深深思索。
同时宗白华的生命美学也格外推崇孟子这种灌注“浩然之气”的充实之美。他说:“文艺境界的广大, 和人生同其广大;它的深邃, 和人生同其深邃, 这是多么丰富、充实!孟子曰:‘充实之谓美。’这话当作如是观。”宗白华认为, 最能表现这种生命精神的人生现象当推文艺活动, 因为文艺活动作为美的展示, 它“所表现的是生命的内核, 是生命内部最深的动, 是至动而有条理的生命情调”。宗白华的美学就是将这种生命情调给予诗意地呈现, 并深深灌注了那种“浩然”、“充实”, 行云流水般的诗情画意, 使之蕴聚着生命的节律, 也体现着中国美学精神的本真。孟子从生命活动的节律动态的角度, 透视“生命内部最深的动”, 把“气”从原本的“自然元气”状态, 超越为内涵伦理道德意义的, 具有人的精神品格的“浩然之气”, 又进一步升华为“充实而有光辉”的“大美”境界, 进而思考对生存的关怀意义, 这种贡献无疑是巨大的。今日, 我们探讨孟子的这种生命智慧, 深刻反思当下人的现实生存状态, 体味在现实功利状态下人们的生存境遇, 启示我们如何寻求超越一般的功利欲望, 追索对生命存在的终极关怀, 无疑也是有意义的。
标签: 生命 孟子 充实 美学 审美